
每日上新
查看更多

仲夏物語
西藏游玩缺氧時,男友把最后兩瓶氧氣都給了姜窈窈。 我剛要質問,眼前飄過了彈幕。 【寶寶,喝可樂也可以緩解高反的,你別怪宋祁,他也為難。】 【是啊,姜窈窈喜歡他那麼久,一直不求回報對他好,如今又是跟他出來旅游才高反的,他肯定要把氧氣瓶給她啊,不然出了事他沒法交代。但這也恰恰證明了,宋祁心底跟你更親近,所以不跟你客套。】 【妹寶,你快抱抱宋祁吧,他擔心你擔心得要死,怕你怪他,只能湊在姜窈窈身邊,其實他眼神一直盯在你身上。】 我盯著湊在姜窈窈身旁,又是擰可樂瓶,又是遞葡萄糖的宋祁,諷刺一笑。 轉身坐上了去醫院的出租車。 宋祁眉頭緊皺:「窈窈身體不舒服,你能不能別讓我為難?」 能的。 我這人最不愿麻煩別人。 所以當晚我就轉機去了新疆。 1 坐出租車去醫院的路上,彈幕急壞了。 【妹寶,求求你,別讓宋祁為難好不好?你們青梅竹馬一起長大,他最在意的人就是你。高三這年,他也是為了提高成績,可以跟你上同一所大學,所以才讓女配給他補課的。】 【對啊,你藝考一培訓就是好幾個月,這期間,要不是女配天天陪著他,宋祁也考不上清大。就算為了報恩,宋祁肯定要照顧好女配啊,但在宋祁心底,你才是自己人。】 【妹寶,讓師傅調頭吧,不就是有些高反嗎?至于這麼大的反應嗎?你這一走,不是給女配制造機會嗎?】 我渾身無力,噁心想吐。 再看到彈幕說的,不就是有些高反嗎? 我差點被噁心得直接吐出來。 他們在說什麼屁話?高反嚴重是能要命的。 今早出發去納木錯的時候,我裝了六瓶氧氣罐在背包里。 可姜窈窈看見宋祁自然而然接過我的背包時,竟然把氧氣瓶都從我包里取了出來。 「嵐嵐,宋祁一個人要背三個包,你怎麼就不能體諒他一下?咱們到拉薩這兩天也沒有高反啊,何必要增加負重?」 我堅持。 「可我做攻略,納木錯海拔四千多米,像我們初來乍到,很容易中招。」 瞥了一眼她包里裝滿的衣裙和化妝品,我隱晦提醒:「其實你帶一套裙子換著穿,拍拍照就行了,沒必要帶七八套,我們出來主要看風景的。」 但她卻瞬間紅了眼:「我知道,你家里有錢,從小四處旅游,覺得我拍游客照很傻。但我從來沒出來過,我只是想跟我朋友分享一下,有錯嗎?」 宋祁立馬打圓場:「拍拍拍,我們窈窈大美女這麼好看,必須出片!氧氣帶兩瓶意思一下就行了。」 他湊到我跟前作揖求饒:「嵐嵐,出來玩,開心最重要。」 想起這趟路程是為了緩解我們之間劍拔弩張的關系,我嘆口氣。 罷了罷了,兩瓶就兩瓶吧,萬一遇到緊急情況還能應個急。 到地方后,姜窈窈不知疲倦,一遍又一遍換衣裙、換妝造,宋祁像個職業攝影師,一直跟在她身后,拍拍拍。 我好幾次想發火,但想著這趟出行的目的,都勉強忍了下來。 其實自從高三那年,姜窈窈搬進宋祁家,我和宋祁之間的關系就開始變緊張。 我那時候忙集訓、忙藝考,好不容易有時間約宋祁出門玩,姜窈窈都會跟在旁邊。 我們看電影,她怯懦開口:「我從來沒去電影院看過電影,嵐嵐,你把我當空氣就好了。」 可她膽子小,明明是普通的探案劇,她卻在看到尸💀時,死死抓住宋祁的胳膊:「宋祁,我好害怕。」 「宋祁,我暈血!」 「宋祁······」 一場電影,宋祁顧不上跟我有任何交流,全程都在安撫驚慌過度的姜窈窈。 我請宋祁吃新開的火鍋店,她眼巴巴跟著:「宋祁最近腸胃不舒服,阿姨讓我盯著他不能吃辣。」 我無奈解釋:「我們吃鴛鴦鍋。」 但她好像聽不懂我的弦外之音:「我必須親眼看著他,不然我無法對阿姨交代。」 #大女主
我嫁給克妻的紈绔后
皇后把我賜給她那死了三任妻子的紈绔侄子。 都怪我裝得太好了。 洞房花燭,楚天瑯居然說要去陪他那柔弱不能自理的寵妾。 我扒光他的衣裳,將他掛在橫梁上。 「你敢下我的面子,我就敢剝你的里子。」 「姑奶奶我有的是力氣和手段!」 1 賜婚圣旨送到將軍府這夜,邱之源求見。 黑暗中,暈黃的燈光下,他彎著腰,雙手捧著我們的定情玉佩,我看不清他的臉,也失去了聽他解釋不得已退婚的苦衷。 皇權之下,他與我皆是螻蟻。 兩家富貴、數百人命,也不過是帝王一句話的事情。 若他聽我的早些成親,便可讓我免去這無妄之災。 伸手抓過玉佩,將他摁在墻壁上親。 他嘴里嘟囔著昭瑜不可如此。 卻不掙扎,也不推開我。 我揚手扇他兩巴掌。 拒絕就要拒絕得徹底,說不要就不要,伸什麼舌頭。 兩塊鴛鴦玉佩在他面前摔得稀碎。 我多一個眼神沒給他,也沒留句祝福的話給他。 任由他低低悲戚地喊著:「昭瑜,昭瑜。」 唉。 我嘆息一聲。 真可惜。 邱之源長得真的很俊俏,身邊也沒通房,沒小妾,潔身自好得很。 我費了好些心思,裝得賢良淑德,才讓他上鉤,哄著他跟我私定終身。 可惜裝過ƭűₗ頭,讓皇后給相中我,賜婚給她的侄子楚天瑯。 說起楚天瑯這浪蕩子,三天三夜都說不完。 撇去他從小沒有母親之外,簡直就是個敗類、禽獸,說他是豬狗,都侮辱了豬狗。 說起這樣子的人,都覺得臟了我的嘴。 可偏偏這種骯臟東西,他即將成為我的夫。 一腳踢開房門,丫鬟們早退避三舍。 我院子下有一間石室,我沿著臺階走下,鐵鍋里粗大的棉線燒得正旺。 照著三個哥哥緊張懼怕的臉。 「妹妹,下手輕些,給哥哥留條命,別讓父母白髮人送黑髮人。」 「呵……」 又氣又恨又能如何,總不能把三個親哥打死。 不過…… 三個哥哥不能打死,要楚天瑯死的方法卻有很多。 我與楚天瑯的婚期定在十月。 皇后賞賜很多,國公府給的聘禮也很多。 這期間楚天瑯又納了兩個嬌妾,又傳出他后院四個妾室有身孕。 加上他前頭三個夫人留下的五個嫡子女。 也就是說,我進門就成了十幾二十個孩子的嫡母。 我一個人笑得有些癲。 母親為此發愁,鬢角好似都多了白髮。 「母親放寬心,嫁誰不是嫁。他有那麼多孩子,就沒人催我生了。」 換言之,就是不用跟這臟東西同房,也不用承受生育之苦,簡直不要太妙。 「我的兒啊,都怪我,想著多留你在身邊,早知道,早知道……」 「母親!」 有些事情可以與父親說,卻不能與柔弱、多愁善感的母親說。 事以密成。 嫁人前,我放縱自己,去勾欄聽曲。 品著萬金難求的茶,心道怪不得男人都喜歡這銷金窟,我也喜歡。 也是湊巧,楚天瑯一行紈绔包下了隔壁雅間。 談笑間,有人奉承道:「世子爺好福氣,那謝家小姐可是個美人吶。」 「呵,謝昭瑜呀,美則美矣,若不是姑姑賜婚,就她,給我提鞋都不配。」 「且她跟邱之源定親好幾年,誰知道還是不是清白之身……」 楚天瑯聲音輕浮,又帶著嫌棄。 「世子爺以后多納幾房美妾,夜夜做新郎。」 「世子爺,小人有個妙計……」 夜夜做新郎? 想得挺美。 #爽文
要她上鉤
校草發了一張貓項圈照片,配文: 【找主人。】 當晚,我就加上了他好友,買齊了所有貓貓用品。 興致勃勃地敲響了他家門。 開門的,卻是戴著項圈的校草。 「貓在哪?」 校草遲疑了一瞬,「喵?」 1 貓癮犯了。 周末回家,把朋友養的那只很好欺負的蓬松吐司大面包揉搓了個遍。 直到它發出不滿的喵喵聲,我才戀戀不舍地松開手。 回去的路上,我在家庭群里提議要養一只貓。 我媽義正辭嚴地拒絕, 【不可能,養你一個就夠費勁了。】 【你還有一年才畢業,也就周末回家當鏟屎官,平日里不還是我和你爸收拾的?】 我爸更是轉發了五條短視頻進行抗議。 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,轉發了十余條養貓的好處短視頻。 一個小時后,爸媽雙雙敗下陣來。 【行吧,你自己要養的,錢要你自己出。】 我使出渾身解數,又朝群里發了幾條撒嬌語音。 最后這件事以爸媽各轉了一筆啟動資金給我告終。 接下來要做的,就是挑選小貓。 其實我早就想好了,要撿一只小流浪回來養。 沒打算養貓的時候,學校里遍地都是流浪貓。 一打算養貓了,卻連貓的影子都找不著了。 還是室友給我出了個主意。 「我記得我們學校有個動物保護社,你可以關注他們的賬號,有需要領養的小貓的話,應該會及時更新消息。」 「對了。」 室友用手肘戳了戳我,笑得神秘, 「聽說林覺溪也在哦。」 我記得林覺溪這個名字,當初剛入學,林覺溪作為新生代表發言。 光是憑借著幾張模糊的照片就傳遍了全校。 後來我們進了同一個社團,雖然沒說上過幾句話,但他給我的印象一直不錯。 沒想到校草還挺有愛心的。 我關注了動物保護社的賬號。 又順著這個賬號關注,找到了林覺溪。 他的主頁很干凈,全是小貓照片,偶爾會露出一雙骨節分明的手。 評論和點贊量都不少。 我日復一日地在他每條作品底下評論,次次消息都被淹沒。 皇天不負有心人,終于有一次,我刷新到了林覺溪的新動態。 他發了一張項圈的照片。 配文:【找主人。】 #甜文
頂級陽謀:給父親的「貞節牌坊」
母親尸骨未寒,父親就扒了我的喪服,套上紅衣送入宮中。 我卻逢人便說父親待我如珠如寶。 為了在拍賣行爭搶一株人參給爹爹補身子,不惜和公主鬧到了皇上面前。 自此之后天下皆知,趙大善人,白手起家,思念亡妻,潔身自好,寵愛獨女。 他一度在民間被標榜為丈夫的典范。 陛下親賜「德沛慈深」金匾。 他死后,兩個男人哭喊著要摔靈認爹。 我眼皮都未抬:「打出去!」 「笑話,父親哪有外室子,你們分明是想給陛下御賜的金匾潑臟水,此乃對我父一生清名之褻瀆,更是對陛下天恩之褻瀆。」 1 冰冷堅硬的棺木硌得骨頭生疼,我卻死死抱著,因為里面躺著我的阿娘啊。 「爹求您讓女兒送完娘親最后一程吧…」我幾乎用盡了全身力氣,從齒縫里擠出破碎的哀求。 父親那張平日里總是帶著溫和笑意的臉,此刻只剩下冷漠和不耐煩。 「胡鬧!」 「能陪長公主遠行,是多少人求不來的福氣,這是光耀我趙家門楣的大事!由不得你任性!」 光耀門楣? 我娘尸骨未寒,靈柩就停在眼前! 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清他眼底的涼薄。 原來我以為的爹娘「相敬如賓」,不過是母親一廂情愿的維系。 「爹,」 「可陛下都允了緩些時日……」 「你懂什麼,正因你娘不在了,你才更要抓住這機會!」 他打斷我,毫無溫度的目光掃過靈柩,像是在掃除一件礙眼的舊物。 「再拖下去,誰知道這恩典還在不在?起來!」 他不耐煩地朝旁邊使了個眼色。 幾個粗壯的仆婦立刻圍了上來,帶著不容抗拒的力道,開始用力掰我摳在棺木邊緣的手指。 指甲刮過堅硬的木頭,發出刺耳的聲響,一陣鉆心的疼。 我的哭喊和哀求被她們完全無視。 「滾開!別碰我!」 父親走了過來。 他俯下身,那雙曾經也抱過我的手,此刻帶著不容置疑的蠻橫,一根,一根,掰開我死死扒住棺木的手指。 每一根手指被強行剝離,都像連皮帶肉撕扯開我對母親最后一點微薄的守護。 仆婦們趁機撲上Ṭū₂來,粗暴地扒掉我身上素白的喪服,將一件刺目的大紅的宮裝硬生生套在我身上。 我被連拖帶拽地塞進那頂冰冷的轎子。 轎簾落下,隔絕了靈堂里最后一點燭火的光。 一片令人窒息的黑暗里,透過縫隙,最后一眼死死盯住轎簾縫隙外,那高懸的、象征著趙家煊赫的牌匾。 2 「背挺直!腰是死的嗎?」 「啪!」 教鞭狠狠抽在小腿上,踉蹌了一下,汗水沿著額角滑落,滴進眼睛,又澀又疼。 「手!托穩!高了一寸,你是要燙死貴人?」 又是一鞭,精準地抽在托著茶盞的手腕上。 滾燙的茶水濺出來,手背立刻紅了一片,火辣辣地疼。 我屏住呼吸,將快要脫手的茶盞重新端平。 短短半月,身上早已沒一塊好皮。 青紫的鞭痕交錯著,碰一下都鉆心地疼。 夜里獨自蜷縮在冰冷的硬榻上,對著窗外的月光,只能一遍遍摩挲著娘親留給我的一方舊帕子。 那上面殘留的、幾乎淡不可聞的馨香,是我唯一能抓住的暖意。 我把這近乎虐待的嚴苛,歸結于孫姑姑對娘親驟然離逝的痛心,或許還有一絲對我這個「不成器」故人之女的失望。 終于捱到了出使前七日,宮里開恩,許我們這些陪嫁女使,在晚宴前歸家一趟。 宮門一開,我便沖了出去,下了馬車,就將裝著換洗衣物的包袱隨手甩給迎上來的老管家。 「不必通傳,我去給娘親上炷香!」 話音未落,人已朝著祠堂的方向奔去。 包袱散落一地,管家在身后焦急地喊著什麼,我充耳不聞。 只想快一點,再快一點,回到娘親靈前,說說這半個月的委屈和思念。 一路小跑,髮髻都散亂了,我卻在祠堂緊閉的朱紅大門前猛地剎住腳步。 里面……有聲音? 不是誦經聲,也不是仆役打掃的動靜。 是一種令人作嘔的喘息和低笑,斷斷續續地從門縫里鉆出來,還夾雜著女人嬌媚的嗔怪。
與皇上珠胎暗結后
選妃前,我被診出了喜脈,家族一致幫我隱瞞。 庶妹卻在宮宴上故意替我擋酒:「我姐姐懷孕了,喝不了酒!」 她驚覺自己說錯了話,連忙告罪:「皇上饒命,姐姐醉酒被奸夫破了身子,她不是故意失貞的!」 「求皇上懲治奸夫就行,千萬不要懲罰姐姐啊!」 座上的皇帝神情冷肅。 庶妹得意挑眉,所有人都以為皇帝要大發雷霆處死我。 其實皇帝只是擔心我動了胎氣。 畢竟那晚的奸夫——就是皇上本人。 1 宮宴尾聲,按規矩是要一起向太皇太后敬酒。 我剛端起杯盞,坐在一旁的妹妹陸頌玉忽然抬手打翻了我的杯子,高聲道: 「姐姐,你懷孕了,不能喝酒!」 此言一出,滿座都朝我這邊看來。 陸頌玉立刻擺出一副惹禍的無辜神情,用右手打了自己嘴一下:「我真笨,又說錯話了!」 我盯著被打翻在地的杯子——我的杯子里本來就是白水。 陸頌玉剛剛也飲了壺中水——她明知道不是酒。 她小聲朝我賠罪:「姐姐,你不會怪我吧?」 這時,主位上的太皇太后追問:「你剛剛說什麼?誰懷孕了?」 太皇太后年逾花甲,頭髮半白卻精神矍鑠。 此事本該由太后主持,可惜太后與先帝一起慘死在當年那場宮變中。 新帝的選妃只能由太皇太后親自主持。 太皇太后越氏年輕時是個厲害人物,她眼底下可容不得沙子。 陸頌玉忙走到殿中間,跪地回話:「啟稟太皇太后,我剛剛說的是——我嫡姐陸頌月懷孕了!」 她的位置離太皇太后很遠,本可以推說是口誤或是聽錯了。 陸頌玉卻不狡辯,還十分誠實地看向我:「姐姐,你別怪我,太皇太后問了,你懷孕的事我不敢欺瞞。」 「陸頌月,你身為皇上的秀女,當真懷孕了嗎?」 新帝選妃,我和今日在場的一眾貴女一樣都是新帝后宮的預選秀女。 選秀前懷孕,是欺君重罪。 我連忙上前回話道:「啟稟太皇太后,臣女沒有懷孕,臣女的妹妹醉酒失言,太皇太后不可當真。」 「我沒有醉酒。」陸頌玉高聲說:「姐姐,事已至此,你怎麼還在太皇太后面前撒謊呢?!」 我怒瞪陸頌玉。 陸頌玉是姨娘所出的二小姐,是我同父異母的庶妹。 兩個月前,我去廟里上香,回來時衣衫破亂,手腕的守宮砂消失了。 爹娘大怒,追問是誰玷污了我。 我想起那個男人的叮囑,咬死說沒看清。 那時我已經在選秀名單上,無論如何也運作不了。 更讓我爹娘崩潰的是,選秀宮宴的前三天,我被大夫診出了喜脈。 這下我爹急得直上火,本想讓大夫開藥將胎兒墮下,太醫說我自小體弱,輕易墮胎恐怕危及性命。 何況選秀近在眼前,一旦墮胎,勢必身體虧虛,到時候一進宮就會被人瞧出端倪,更是此地無銀三百兩。 爹娘無計可施,只能商定,千萬不能被人知道我選秀前失貞一事,讓我照常參選。 又叮囑我在選秀時故意露怯露拙,只要不被皇上看上,一切都還有轉圜余地。 等我落選,他們會對外稱我落選傷心生了病,把我送去鄉下,屆時才能處理腹中胎兒一事。 應對之法商定后,父親對要與我一同參選的二女兒陸頌玉再三叮囑: 「大家族一榮俱榮、一損俱損,你姐姐失貞懷孕一事,你千萬不可說漏嘴,否則就是拉著整個陸家一起死。」 陸頌玉明面上鄭重答應,卻在今日宮宴上,故意打翻了我的杯盞,說漏了嘴。 她絲毫不懼我的眼神警告,繼續告狀: 「太皇太后,臣女不敢欺瞞您,我姐姐她就是懷孕了! 「兩個月前,我姐姐去紫寧寺上香回來,我便看見她下身衣衫凌亂,四肢和脖頸都有曖昧淤痕,必然是被外男欺負了。 「我們全家都追問姐姐是誰禍害了她,可姐姐咬死說她記不清當日之事,更記不清玷污她的狂徒是誰。 「姐姐如此維護那個奸夫,想必是與她兩情相悅的情郎吧……」 「臣女心里實在害怕,我不能看著姐姐拿這副不貞之軀參選秀女欺瞞君上。」 「姐姐才貌出眾,萬一被皇上選中,那她豈不是要懷著……懷著奸夫的野種進宮侍君?」 2 此言一出,太皇太后神色大變。 在場其他貴女紛紛打量我,議論我: 「真是膽大包天,她這是想把腹中孩子賴給皇上不成?」 「這可是欺君大罪,陸頌月不想活了!」 我高聲辯解:「啟稟太皇太后,臣女是皇上的秀女,沒有失貞,沒有奸夫,更沒有野種一說!」 「姐姐還在撒謊!你若沒有失貞,就把你的守宮砂亮出來給太皇太后過目啊!」 陸頌玉說著先撩起自己的右手衣袖,露出那枚鮮艷的紅色守宮砂。 守宮砂自女子出生起就點在手腕上以示清白,一旦失貞,守宮砂消失,再不可能重新點上。 陸頌玉是我的親姐妹,她如此揭發我,太皇太后立刻起疑,下令要我自證清白。 我緊緊握著右手手腕向后退了兩步,被兩個魁梧的嬤嬤攔住去路,扣住胳膊。 我的衣ţů⁷袖被嬤嬤粗暴地撩起,卻見手腕上——赫然有一顆鮮艷的守宮砂! 守宮砂消失的那一晚,母親就用朱砂重新替我點了一顆紅痣,試圖以此掩人耳目,躲過選秀前的檢查。 母親偽造的這顆守宮砂與在場其他貴女的守宮砂肉眼看別無二致。 太皇太后見此,正要打消疑心,陸頌玉卻忽然大聲道: 「太皇太后,您別被她騙了!她這顆守宮砂是陸家人給她偽造的!不信,拿皂角水來!」 太皇太后讓人備了皂角水,陸頌玉用手帕沾了水,就要往我手上那顆朱砂擦去。 我低聲質問:「陸頌玉,你瘋了,你是要拖著陸家一起死嗎?!」 陸頌玉嗤笑,用只有我能聽見的聲音挑釁:「什麼一榮俱榮一損俱損?只要把你推下去,我就一定能中選為妃,到時候陸家得靠著我平步青云!」 「你胡說什……」 我這時才注意到,陸頌玉的脖頸間,掛著一顆東珠項鏈,只看色澤,便知是御賜之物。 陸頌玉順著我的視線摸上自己脖頸間的珍珠: 「知道我為什麼不怕被你拖累嗎?因為皇上早就看中了我。」 「這兩個月來,他一直派人私下贈我信件珠寶,還給我溫補的良藥。」 陸頌玉面露得意的嬌羞之色: 「我明白陛下的意思,他是想讓我溫補好氣色,再穿得漂漂亮亮地來宮里見他。」 #大女主
竹馬日記
我竹馬小時候總喜歡偷看我的日記。 為了教訓他,我偷偷在日記里寫到—— 「媽媽告訴我,我跟顧陳年其實都是她生的,只是顧陳年太調皮,才被送到顧叔叔家,顧叔叔是警察,能管得住他……」 從那以后,顧陳年對我的態度變了。 好吃的給我先吃,好玩的給我先玩。 有人欺負我,他就幫我揍回去。 他把我當成了親妹妹一樣保護。 直到高中畢業,班里男同學跟我表白。 眾人起哄,顧陳年卻悄然離開。 他喝得爛醉,在路邊耍酒瘋。 我過去找他,被他一把推開:「我不配你對我這麼好!」 顧陳年看著我,眼神說不出的悲涼:「我居然喜歡上自己的親妹妹,我真不是東西!」 我:「?」 1 高考完的暑假,大家都玩瘋了。 雖然已經畢業,但班級群卻仍然熱鬧。 大家準備在開學前最后聚一次,地點就定在我們常去的一家土菜館。 閨蜜發消息問我:「到時候你怎麼去?要我騎車接你不?」 我:「不用,顧陳年騎車送我去。」 閨蜜宋余「嘖」了一聲。 「別的不說,你這竹馬真是讓人羨慕啊。」 她細數我們高中三年。 「不僅人長得帥,每天早上有人送你上學,給你接熱水。」 「你生病了他第一時間送你去校醫院,寸步不離地守著你。」 「咱們班晚自習放得晚一點,他就一直等你,然后把你安全送回家,還有你每年生日,他都會給你準備禮物……」 宋余感嘆:「真是羨慕不來。」 我有點小得意,嘴里卻還說著:「也沒有啦。」 …… 我跟顧陳年六歲就認識了,我們是門對門的鄰居,又在一個幼兒園上學。 雙方父母非常合得來,常常互相串門。 時間久了,我跟顧陳年就成了最好的朋友和伙伴。 但他有時候很皮,喜歡揪我的辮子,還故意躲起來嚇我。 我被嚇哭了,他也被他媽媽拎回去教訓。 我聽見他媽媽說:「不能欺負妹妹!」 顧陳年明明已經知道錯了,卻還嘴硬:「妹妹不能欺負,她又不是妹妹。」 在他的概念里,只有一個媽媽生的妹妹,才是他真正的妹妹。 我們就這樣打打鬧鬧到了小學三年級。 顧陳年又多了一個壞毛病。 他喜歡偷看我的日記。 光看還不滿足,還喜歡把我寫的日記告訴別人。 我氣壞了。 決定教訓教訓他。 于是在某天的日記里寫到:「今天媽媽告訴我一個秘密,其實,顧陳年跟我都是她生的小孩,顧陳年比我大一點,是我的哥哥,可他太調皮了,媽媽管不住他,所以把他送給了顧叔叔,顧叔叔是警察,可厲害了……」 「媽媽說,顧叔叔和李阿姨已經把他當成了親生兒子,所以這個秘密不能讓顧陳年知道,即使他有一天發現了,大家也不會承認,唉,我真是沒想到,顧陳年居然是我的親哥哥……」 顧陳年果然偷看了。 那天上課,他整個人心不在焉,還被老師打了手心。 回去的路上也一言不發,只是會偷偷用復雜的眼神打量我。 但這篇日記,效果顯著。 顧陳年把我當成了他親妹妹,不僅給我送吃送喝,還幫我教訓那些欺負我的小男孩。 小大人似地拍了拍胸口:「安瑤你放心,以后我保護你!」 2 我猜到,顧陳年在一兩個月后就發現了我寫日記騙他的這事。 畢竟,一般有點智商的人都能猜出來,這只是個惡作劇。 可顧陳年沒來找我算賬。 反而把保護我、照顧我這件事當成了習慣。 一做,就是許多年。 從小學,到初中,到高中。 成了現在獨屬于我的,人人艷羨的竹馬。 …… 顧陳年高中跟我不是一個班,他騎車把我送到聚會的地方:「結束了跟我說,我來接你。」 我取下安全帽遞給他:「好。」 今天太陽挺大,顧陳年也摘了安全帽,抓了兩下被汗浸濕的頭髮。 他長得很白,一雙微微上挑的桃花眼總是顯得很多情。 陽光照在他臉上,顧陳年瞇了瞇眼。 他正要走時,被我們班男生看到,幾個人熱情地跑過來,連拖帶拽把他給拉到包廂了。 「客氣啥,大家都認識!」 「就是,顧陳年你雖然是隔壁班的,可你來我們班來得那麼勤,誰不認識你?!」 顧陳年不是扭捏的性子,見他們這麼說,也不走了,大大方方坐下來。 高中畢業了,大家仿佛一下子成熟了。 也可能是裝的。 他們點了一箱啤酒,一邊喝一邊侃天侃地。 顧陳年不動聲色地把別人ţŭ⁹遞給我的酒盡數擋下。 「她還有半個月才滿十八歲,還不能喝酒。」 他自己反而一杯接著一杯。 我提醒他:「待會不騎車了?」 「打車回去。」 「那你也少喝點。」 顧陳年笑了笑:「知道了,你好啰嗦。」 聚會進行到最后,氣氛從一開始的熱情興奮變得有些傷感。 班長說:「這可能是我們有些人這輩子最后一次見面了,如果大家還有什麼話想說,就盡管說吧,免得給自己留遺憾。」 我正沉浸在離別的氣氛里,包廂的燈突然滅了。 我嚇了一跳,下意識抓住了顧陳年的手。 他拍了拍我的手背,小聲道:「沒事。」 下一瞬,有人捧著蛋糕和鮮花進來。 包廂里光線模糊,可我還是看清了他的臉。 我的同桌,許然。 許然耳朵紅透了,他將點著明亮蠟燭的蛋糕放在我面前:「安瑤,雖然你的生日還沒到,可我還是提前祝你生țŭ⁸日快樂。」 我怔愣地看著他。 而顧陳年,也悄悄松開了我的手。 「安瑤,如果你愿意,等你真正生日的那天,我也可以陪你一起過。」 「喔~」眾人起哄歡呼。 這歡呼給了許然莫大的勇氣,他把花遞向我:「我喜歡你,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嗎?」 我被幾個女生拉起來,站在了許然面前。 一時間,腦子一片空白。 幾乎下意識地,我看向顧陳年,卻發現,他不知道什麼時候離開了包廂。 甚至,沒跟我說一聲。

今日點擊榜
查看更多

重生后,放任老公追求真愛
女兒滿月宴,老公聽到初戀離婚的消息。 當場喝得爛醉,要連夜開車一千多公里去接人。 「她還愛我,她什麼都沒有了,她在等我!」 我忍淚咬牙叫來公婆,提出離婚。 當晚他沒有走成。 第二天,他看到初戀✂️腕的朋友圈。 發瘋把女兒拎到陽臺外: 「唐荔,我也讓你嘗嘗痛失至愛的滋味。」 我撲過去搶女兒,卻被他一起推下樓。 落地的剎那,我又抱著女兒在滿月宴上。 這一次,我讓他去追愛。 他卻殘疾慘死,連發瘋都做不到了呢。 1 宴席接近尾聲,我和老公陸定嶼正忙著送客。 只剩他的老同學一桌還在喝酒,不時有議論聲傳來。 「哎,我這兒有個大瓜。溫若可今天離婚,你們還不知道吧?」 「她不是嫁挺好的嘛,怎麼突然離了?」 「好個屁,到有錢人家當保姆而已。」 「不好也是她活該,如果嫁給定嶼能有今天?」 「當初都以為她們要從校服到婚紗,在座的當年誰沒羨慕過定嶼啊。」 我晃了晃身子,緊緊抱著失而復得的女兒。 前一刻墜樓的失重感,讓我雙腿發軟,幾乎站立不住。 可陸定嶼的心神全被那些話吸引過去,根本沒覺察到我的異常。 「唐荔,你先帶寶寶回家,我去跟他們喝幾杯。」 不等我答應,他就端了酒,故作輕松地走過去: 「你們剛剛在聊溫若可?她怎麼了?」 我先一步回家。 提前寫好離婚協議等著。 天黑后,陸定嶼果然喝得七八分醉,被人送回來。 見面就撲到我面前: 「唐荔,對不起!」 然后抓起車鑰匙,東倒西歪地往外走。 我搶掉他的車鑰匙,問他去哪兒。 他就借酒裝瘋: 「我要去找若可,她還愛我,她在等我。」 陸定嶼和我談戀愛期間,沒有主動提過溫若可分毫,信誓旦旦只愛我一個。 我從別人口中聽說他們的曾經,也介意過。 他卻從多方面證明,兩人從來沒有過任何聯系。 他會在下雨時為我撐傘,生病時給我熬湯,危險時擋在我前面…… 懷孕、生產時,他對我也無微不至。 他讓我堅信,我們的愛情是雙向奔赴。 我身邊的同事、家人,都稱贊他是個不可多得的好老公。 所以,前世我聽到他的話,震驚、心痛! 甚至歇斯底里! 搶掉車鑰匙把門鎖死,拉著他不停追問,愛情為什麼會突然消失。 他胡亂地把手機翻出來,推到我面前,向我證實溫若可對他的愛。 然后在我面前乞求: 「我要去找若可,她在等我。 「她沒有親人、朋友,什麼都沒有,她只有我。」 我腦子里亂如麻,心里像被萬蟻啃噬。 打電話叫來住在同小區的公婆。 當著他們的面,對陸定嶼說: 「要走可以,先把離婚協議簽了。」 婆婆不停打他,罵他。 公公端了盆冷水往他臉上潑。 他任打任罵,像個沒有靈魂的木偶。 第二天,他酒醒后發誓會向我好好認錯,把公婆哄出門。 轉頭卻趁我給女兒泡牛奶,抱起女兒沖到陽臺上。 「唐荔,若可今天早上✂️腕了,你高興了嗎?」 陸定嶼雙眸通紅,唇角勾起殘忍。 一只手抓住女兒的衣服,把小小的她懸在陽臺外面。 我嚇壞了,沖到他身邊卻不敢激怒他。 「溫若可✂️腕Ŧū́⁽……她,她能告訴你,肯定還沒死。 「你快點去找她,把孩子還我!」 女兒的臉被勒得發紫,發出小貓一樣的嗚咽。 陸定嶼猙獰地對我吼: 「她✂️腕了,你聽不懂嗎?都是你害的,都怪你! 「唐荔,我也要讓你嘗嘗痛失至愛的滋味!」 他故意把女兒抬高,在我面前晃了晃。 我飛身撲過去,想把女兒搶回來,卻被他一起推下樓: 「這麼急,就一起去給若可贖罪!」 我急速下墜,卻怎麼都抓不到女兒…… 落地的剎那竟重新抱著她在滿月宴。 幸好,現在都還來得及。 這一次,我成全他們! 我倒想看看一無所有的他,能不能有情飲水飽。 死算什麼?生不如死才更難受! 2 「唐荔,把門打開,車鑰匙給我。別逼我對你動粗!」 陸定嶼在我面前叫囂,把我從思緒中拉出來。 我沒有像前世那樣,給公婆打電話。 調轉方向,對著在他進門之前,提前打開錄音錄像功能的監控。 開始我真情流露的表演! 拉住他淚如雨下,聽他表明對溫若可的心意,悲傷地問他: 「那我算什麼? 「我們的曾經又算什麼? 「你到底有沒有愛過我?」 他怔了怔: 「別問了!我不知道!」 隨后搖搖晃晃地把手機遞到我面前: 「我只知道若可需要我。」 我顫著手,在他手機上輸入自己的生日,打開鎖屏。 界面停在溫若可朋友圈最近的發文: 【一無所有,只念曾經!】 【我有一個夢:那個曾經說要給我家的男孩,帶著玫瑰開車來接我。】 【不過,只是夢罷了。】 【這世界似乎也沒什麼可留戀……】 我拍下溫若可的朋友圈。 做足了把我自己摘出來的準備。 決絕地拿出兩份協議,死死抱住他威脅: 「我和女兒加在一起都比不過溫若可,那就離婚! 「你同意房子、車子、孩子、公司和存款全歸我,我就讓你走。」 他立即搶過協議,看也不看。 迅速在《離婚協議》《股權轉讓協議》上簽字,按下手印。 重重甩到我身上: 「夠了嗎?」 紙張散落一地,女兒在月嫂陳姐懷里大聲哭鬧。 我哭得全身發顫,抖著手去摸車鑰匙和控制門鎖的手機。 他急不可耐地扯著我的衣服,一把搶走。 隨后甩開我摔門離去。 我跌坐在地上,手壓在之前被他砸碎的水杯上,鮮血流出來。 整個人像要碎掉一般,失聲痛哭。 陳姐嘆了一口氣,把女兒放下,蹲在我身邊: 「唐荔,我看看你的傷口。」 我失魂落魄地抱過女兒,跟她一起哭,血糊得到處都是。 陳姐只能幫我把散落的協議撿起來,又把手機遞給我。 「陸先生父母住得不遠,你看要不要把他們叫來?」 我拿到手機后,卻瘋了一樣不停撥打陸定嶼的手機。 直至電話那頭傳來全是忙音,V 信也顯示紅色感嘆號。 「他拉黑我?他就這麼絕情嗎?」 我看向陳姐手中的協議。 突然像瘋子一樣,把寶寶塞給她,搶過協議沖進房間,鎖進我放首飾的保險柜。 外面傳來陳姐打電話的聲音,她在通知我公婆。 我扯了扯頭髮,給做律師的閨密季桐發了消息: 【協議已簽,他父母很快會來。】 季桐立即回復: 【公司股權轉讓先辦,離婚起訴時間長,最好先逼他做離婚登記。】 țůₛ 【閱后立刪!打電話!】 我沒有回復,選中這幾條消息刪除。 陳姐的聲音也在門外響起: 「唐荔,你先出來把傷口包一下吧?我給陸先生爸媽打了電話,他們說馬上過來。」 我像個在游魂一樣,慢悠悠地去開門。 任由陳姐拉回客廳監控的范圍。 繼續我的表演。 簡單處理過傷口后,我撥通季桐的電話大哭: 「桐桐,陸定嶼不要我,也不要寶寶了。我該怎麼辦?」 那頭的季桐義憤填膺: 「什麼?他人呢?我文件落你家了,正好在來取的路上,你等我。」 門鈴也適時響起來。 公婆到了!
不疼,卻一張張割在她心上
夏晚星消失了。起先并沒有人在意,所有人都以為她只是鬧脾氣,用不了多久就會回來,包括程景肆。 可一個月,三個月,五個月,甚至一年,她再也沒有出現。 直到程景肆翻遍了洛城也找不到她的時候,他第一次感受到,他好像徹底失去她了。 「聽說程總跟林氏千金已經定婚期了。」 「我知道,真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。, 「那夏特助怎麼辦?」 「還能怎麼辦?玩膩的東西當然是丟了啊。」 這句話后,里面便傳來一陣心照不宣的笑聲。 夏晚星像被什麼釘在門口。 半響,她轉身進了洗手間。 夏晚星看著鏡中臉色蒼白的自己,強迫自己嘴角扯出一個弧度。 遲早會有這麼一天不是嗎?愛上程景肆的那一刻,她就應該知道。 壓下心底細細密密的疼痛,夏晚星走出洗手間,下一瞬,就被狠狠推在墻上 四目相對,她沉入程景肆深沉眼眸 但程景肆隨即便移開視線,呼吸中帶著酒氣,在她唇上輕啄, 「都聽見了?」 夏晚星白著一張臉,沒有出聲。 「你一向很懂事。」 「剛剛林蓓說,結婚的時候,希望你去當伴娘。」 夏晚星渾身一僵,大腦一片空白。 他怎麼能這麼對她? 她可以接受他的新娘不是她,但絕對受不了以旁觀者的身份親眼見證他的婚禮。 夏晚星不知道自己怎麼回到家里的。 她坐到書桌前,打開電腦。 黑暗的公寓中,只有電腦幽幽的光照在夏晚星蒼白的臉上。 她看了面前的每個字許久許久,終于,僵著手按下了郵件發送按鈕。 三秒后,信箱提示音響起。 --您的‘辭職申請書’已發送至程景肆。 第二天,程景肆踏進頂樓,卻沒在辦公室外看到那個熟悉的人影。 他的眉頭下意識皺了起來,心情莫名的煩悶。 看了眼時間,他吩咐秘書:「告訴夏晚星,10分鐘內不趕到公司,這個月的獎金都扣完。」 「是。」秘書笑著打開工作平板,下一秒,笑卻僵在了臉上。 「程總……」她看著郵件,不知為何有些難以開口。 「怎麼?」程景肆冷冷抬眼。 秘書遞出平板:「夏特助她……辭職了。」 #全文見評論區
萬界無敵
天葬不死,雙珠在手,翻手為仙,覆手為魔。玉塔仙靈,佳人傾國,傲視諸天,群星伴我。 葉秋,一個被送往天葬深淵凈化的垂死之人,卻因為擁有無屬性的命魂珠躲過一劫,反而獲得了天葬深淵隱藏萬古的最大奇遇——仙王封魔。 玉塔從天降,造化育奇功,征戰九天外,宇宙獨尊我。 #長篇 #玄幻 #腦洞 #爽文 #評論區看全文
致命期末考
最后一場期末考,我是監考員。 考試結束,48名學生全員死亡。 警方第一時間鎖定了我。 但是尸檢結果出來,所有學生死于自盡。 沒有辦法,我被無罪釋放。 可三年后,一位醫學生找到了我: 「是你殺的吧?我已經知道你那天給學生們出了什麼題。」 我身體忍不住的顫抖—— 三年,她終于來了。 1 「好吧,是我干的。」 面對這個不速之客,我照常切著肉做今天的午飯。 甚至還轉頭熱情招呼: 「坐吧,正好趕上飯點,我們邊吃邊說。」 林詩婷對我的坦誠有些驚奇,但還是并著腿坐在了桌邊,目光在我的切菜刀上停留了幾秒。 很有防備意識。 不錯。 畢竟我曾經監考過一場無人生還的考試。 雖然警方都找不到我動手的證據,可社會各界早就對我產生了諸多猜測。 甚至還有以我為原型的懸疑電影橫空出世,斬獲多項大獎。 「這幾年找我的人很多,你不是唯一一個。」 我把切好的肉下鍋,調整火候后坐在她對面: 「但是猜到我出了一道題的,你是第一個。」 林舒婷猛地站起身: 「所以你真的出過題!」 我這才意識到——她在詐我。 既然如此,那題目內容,她大概也不知道咯? 于是笑起來: 「你覺得可能嗎?一道題讓48個學生心甘情愿的自盡?」 林舒婷又緩緩坐了回去。 我臉色一變: 「但是我可以。」 「你!」 2 林舒婷是醫學院的學生,三年前那場集體自盡案的尸💀狀況太糟糕,她的醫學院出動了不少法醫學的學生協助尸檢。 林舒婷就是其中之一。 那些尸💀的慘狀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她不相信48個人會同時自盡。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,可以毫無人性的將48個孩子的生命玩弄于股掌之中? 所以三年時間,她搜遍了所有資料,發現那天明明是期末考試,可是從始至終沒有見到試卷。 她大膽猜測,我是自己出了什麼題。 但什麼題可以讓48個孩子集體自盡? 被這個問題折磨三年,她終于找到了我。 沒想到,剛一詐我,我就承認了。 而我,很樂意為她解答。 「可是這怎麼可能?那48個學生都是家境殷實的富二代,善于社交、擁有親情和友情。 「有的人已經獲得了國外名校的offer,甚至有的人已經和女友訂了婚! 「他們每一個人都前途無量、樂觀開朗、樂于助人,他們不可能有尋死的念頭,更沒有一個人有過精神病史,怎麼可能因為你一道題就自盡!」 #懸疑
許諾成空
結婚五年,我和沈敘白一直要不上孩子。 後來,我們做了三年試管。 終于在第八年成功懷上雙胞胎。 可懷孕四個多月時,我無意中聽到他和朋友的對話。 「你患有弱精癥,人家許諾三年時間,前前后后做了七八次試管,人都看老了十幾歲,你居然背著她把婚內大半財產都轉到小情人名下,是不是太狠心了?」 沈敘白毫不在意挑了挑眉。 「如果不是心疼小姑娘做試管要遭罪,我可能早就和她離婚了。」 「你是沒見她現在脫了衣服后的模樣,一身肥肉,懷孕后又滿臉是斑,我看著就倒胃口。」 我低頭看了看手里的孕檢單,轉身去醫院預約了流產手術。 1 做完四維彩超后。 我拿著印著寶寶側臉的彩超照片看了又看。 看著那兩個小小的身子蜷縮成一團,像個小豆莢,心里有說不出的喜歡。 沈敘白這兩天忙著公司的事情,已經有兩天沒有回家。 我迫不及待想把這些照片拿給沈敘白看。 在公司樓下咖啡店買了咖啡,和他最愛吃的海鹽焦糖蛋糕。 前臺小姑娘看見我,熟稔地和我打招呼:「許姐您來啦,沈總現在在辦公室,方先生剛才過來了,他們可能在聊事情。」 我沖她笑著點了點頭,徑直向總裁辦公室走去。 前臺口中的方先生,是方嶼北。 他是我和沈敘白的大學同學,如今和沈敘白有生意往來,他妻子姜茉是我最好的朋友。 我們關系一向不錯,沒什麼好見外的。 剛準備推開辦公室半掩的門,就聽見方嶼北提起我的名字。 「你小子別玩火自焚,這事要是被許諾知道,可不是鬧著玩的。」 我推門的動作頓住。 里面的聲音繼續傳來: 「你患有弱精癥,許諾懷上孩子不容易,我聽小茉說,她這三年為了懷孕,前前后后做了七八次試管,人都看老了十幾歲,你背著她把大半財產轉到葉蓁蓁名下的空殼公司,是不是太狠心了?」 方嶼北滿臉不贊成地看著沈敘白。 沈敘白聽后,卻是煞是玩味地挑挑眉。 「呵!說得好像你對姜茉有多深情似的……」 「我警告你啊,這事千萬別讓姜茉知道,你如果說漏了嘴,傳到許諾耳朵里,這事我和你沒完。」 方嶼北沒再說話。 沈敘白接著道:「這談不上狠不狠心,感情的事,誰能保證在一起就是一輩子。」 「如果不是因為我患有弱精癥,怕小姑娘做試管太遭罪,我去年就跟許諾離婚了。」 「當然,離婚我也不會虧待她,等她生下孩子,我會給她一筆錢,足夠她下半輩子衣食無憂了。」 2 方嶼北沉默了好一會兒,才低聲道: 「不是,你是來真的?逢場作戲我當你解悶,可葉蓁蓁那種女人,她擺明是沖著錢來的。況且你和許諾大學就在一起,我不信你對她完全沒有感情了。」 沈敘白哂笑了一聲,似乎是這個問題太過于愚蠢。 他漫不經心晃了晃手里的水杯:「說完全沒有感情是假的,養只貓狗,久了都會有感情,更何況是活生生的人。」 「但現在嘛……」 沈敘白略帶嫌惡蹙起了眉: 「許諾這幾年胖得不像樣,你是沒見她脫了衣服后的模樣,一身肥肉,懷孕后滿臉是斑,鼻子不知道為什麼,突然也變得很難看,我看著真有些倒胃口。」 「她現在這樣,我帶出去都嫌丟人。」 「既然都要花錢養著,我為什麼不找個年輕漂亮的?起碼帶葉蓁蓁出去,我還能有面子。」 #現實情感

熱門好書 百聽不厭
換一換


最新上線 搶先入耳
查看更多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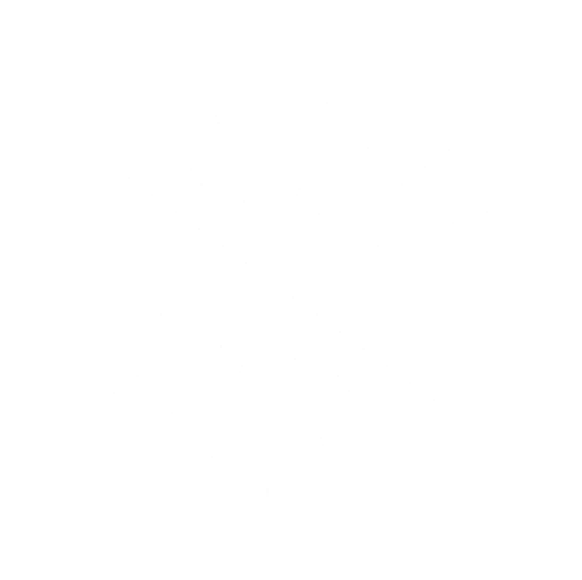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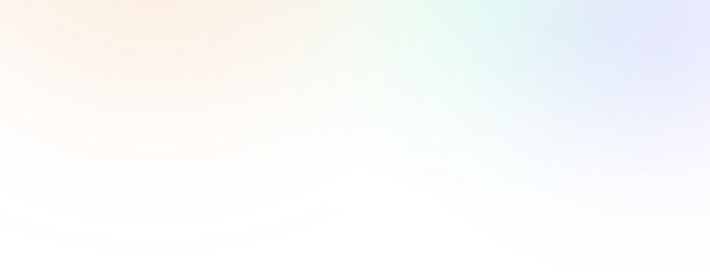
 暢享閲讀盛筵!
暢享閲讀盛筵!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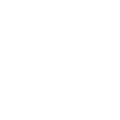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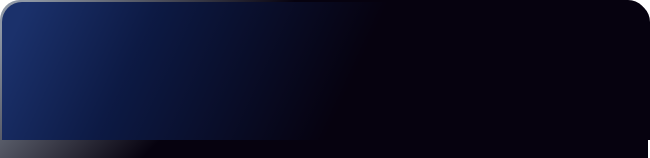





 聯繫客服
聯繫客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