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每日上新
查看更多

熙寧
我和冉讓青梅竹馬,從小我就很聽他的話, 到高中更夸張,幾乎對他唯命是從。 我給他帶的早飯,全被他轉贈給漂亮的貧困生,我不生氣。 貧困生扔了我買的包子,說自己只愛吃油條,我不生氣。 高考后,冉讓更是為了她,跑來警告我: 「藝橙不想跟你上同一所大學,你不許填跟我們一樣的志愿。 「一個地方也不行。」 我依然不生氣。 後來,錄取通知書下來,我如愿被一千公里外的 C 大錄取。 冉讓卻一遍遍地問我為什麼。 他好奇怪啊。 不是他自己要求的嗎? 1 填志愿那天,冉讓忽然來找我。 「我和藝橙都打算報 A 大。」 「然后呢?」我問。 「她不想跟你上同一所大學,所以,你不許報。」 我沉默片刻,不知該不該告訴他。 我就沒打算上 A 大。 可冉讓沒給我開口的機會。 「最好 A 市的學校你都別報,別跟我們去一個地方。」 「藝橙有抑郁癥,你體諒一下。」 我跟冉讓認識十八年了。 從小到大,他說什麼我都答應。 這一次,也不例外。 我笑容燦爛,說:「好啊,都聽你的。」 冉讓蹙了蹙眉,似乎對我的回答,并不滿意。 2 我管他滿不滿意。 報完 C 大的志愿,我躺在床上刷手機。 忽然看到黃藝橙的朋友圈。 「今天,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女孩呀。」 原來是她生日。 但黃藝橙是貧困生,哪來的錢辦生日趴? 翻到評論區,我就明白了。 冉讓說:【你滿意就好。】 黃藝橙:【謝謝你,這是我十八年來過得最開心的一個生日!】 冉讓:【我保證,不會是最后一個。】 正要關閉朋友圈時,我突然看到黃藝橙身上那件粉色禮裙。 很眼熟。 不就是我上個月去訂做的那條嗎? 準備在九月的成人禮上穿的。 當時,是冉讓陪我去量的尺寸。 我還沒去取衣服,怎麼就穿在黃藝橙身上了? 我立刻打電話給冉讓問個清楚。 可他卻說: 「哦,藝橙沒有禮服,臨時做一件也來不及了,我想起來你上次做衣服那家,手藝還不錯。剛好你倆身材差不多,先借給她穿穿。」 要是在以前,我可能真就同意了。 因為我要冉讓的筆記,要他給我講題。 年級第一的解題思路,可比一條裙子重要。 可現在,志愿都報完了,他算那顆蔥? 我不再壓抑怒火: 「沒經過我同意,你憑什麼擅自借給她?!」 冉讓很是意外: 「寧寧,你生氣了?」 「廢話。」 「藝橙的情況你又不是不知道,別那麼小氣。」 「她什麼情況都跟我沒關系!你們擅自拿走我的東西,我要報警!」 「你我兩家條件都不差,有必要這樣嗎?就一條裙子。」 「那條裙子價值超過三千,夠立案了!」 話至此,冉讓終于發現,我變了。 他語氣中也帶了點怒意: 「衣服還你就是了!」 3 半小時后,他倆出現在我家門口。 黃藝橙懷里抱著裙子,裙邊已經染上污漬。 「熙寧,對不起,我沒想到你會這麼介意……」 說著說著,她哭了。 冉讓蹙眉看她,心疼壞了。 「別哭,不就是條裙子,一會兒我也給你買一條。」 然后,他才轉頭看我,神色疏冷。 「藝橙主動道歉了。你是不是也該跟她道個歉?」 「我道什麼歉?」 「她哭得這麼傷心,你就一點都不內疚嗎?」 我沒有回答冉讓。 而是看著黃藝橙,還算溫柔地問:「你喜歡這條裙子嗎?」 黃藝橙哭著點頭。 「那我送你好不好?」 她眼睛一亮,有種占到便宜的得意感。 然而下一秒,我抄起旁邊的剪刀,三兩下,將裙子剪爛。 扔進垃圾桶。 「送你了,撿去吧。」 黃藝橙臉色煞白:「我雖然家里窮,但你也不能這樣侮辱我!」 冉讓也變了臉色。 「有必要這樣嗎?李熙寧,從小到大,我送你的裙子沒有三十條,也有二十條吧?就當是我找你借的。」 「你?更不借。」 我轉身準備關門。 冉讓卻抵住門板,拽著我的手腕。 「寧寧,你是不是因為報志愿那事生我的氣?」 他頓了一頓,語氣有所緩和, 「其實,你如果真跟到 A 市來,我也不會怪你。」 #大女主 #渣男
小盈
我從河里釣了個落難少爺。 少爺難養,吃飯要用象牙筷,喝茶要用白玉杯。 落到我手里,連魚豆腐雞頭米,筍干煨肉醬王瓜,饞得少爺眼巴巴,天天抱著只破碗等開飯。 我托著腮瞧他,「我怎麼記得某人曾經說,就算是餓死,也絕不吃我一口飯?」 少爺盯著鍋里翻滾的薺菜鮮蝦小餛飩,笑容乖巧又諂媚。 「某人說過的話,和我鄔月有什麼關系?」 1 鄔月會在每場春雨后,準時出現在地里挖野菜。 我晨起時,灶上食材碼得滿當當,還帶著泥土的腥氣。 野薺菜。春筍頭。半簍活蹦亂跳的河蝦。 鄔月攏了攏臟兮兮的袖口。 可憐巴巴地望著我。 「……餓。」 很難想象。 眼前這個泥猴子似的人。 曾經是個手臂蹭到一個泥點,都要反復搓洗到破皮的潔癖大少爺。 三個月前,我在河邊釣魚,釣上來個衣著華貴、渾身是血的男人。 我當即兩眼放光,將他背回了家。 鄔大少爺醒來那天。 目光掃過低矮的草屋。 屋里橫行霸道的老母雞。 還有我手中一碗暗綠色的不明糊糊。 又痛苦地閉上了眼睛。 「這位姑娘。」 他的臉色比菜糊還綠。 「要不還是讓我死了吧。」 我大驚。 萬萬不可! 好不容易才讓我撿到了落難貴人。 他要是死了。 我指望誰來報恩呢? 2 施恩圖報,我有私心。 隔壁舒二娘子曾經搭救過一個落難貴人。 後來貴人為了報答,接她進京做妾。 十里八鄉的小娘子個個紅了眼,說她攀上高枝,一輩子享不完的榮華富貴。 我不圖做妾享福,我有心上人的。 只是我心上人沒錢娶我。 今日要給書院的先生交束修,積蓄無多。 明日要和同門喝酒應酬,囊中羞澀。 說來說去,他總在嘆氣。 「小盈,我不愿委屈了你。」 「等我攢夠了錢,一定八抬大轎,風風光光娶你進門。」 我說,好呀沈郎,我等你。 然后我等啊等,等到十九歲。 連八抬大轎的影子都沒瞧見。 沈硯舟還是沒錢娶我。 所以,我想要一點錢,和他一起湊湊聘禮。 沒有八抬大轎。 沒有十里紅妝。 沒有關系。 #美食
又是一年春
蕭徹為了戰場上撿回來的那個女人,打翻我親手熬的湯。 我被燙傷,疼得難以入睡時,他在陪她看花燈。 我忍痛寫下和離書。 卻突然看見彈幕: 「不要啊,男主是有苦衷的!那女人是羌戎奸細,他在逢場作戲啊!」 「女主疼的只是手,男主疼的可是心啊!」 ͏「男主太隱忍了嗚嗚嗚,他那麼愛女主,要是知道女主因為這點小事就要跟他和離該有多傷心,女主怎麼這麼不懂事。」 …… 我拿著和離書出去,剛好碰到他們回來。 蕭徹看著我眼中閃過不忍,緩緩道: 「我剛好有事找你,我要納阿銀為妾。」 我握緊手中的和離書,笑得懂事溫柔: 「好。」 1. 見我答應的這麼快,蕭徹一愣。 他動了動唇,顧及到旁邊依偎著他的阿銀,只問了一句: 「這麼晚了,去哪兒?」 我垂眸: 「有事去找婆母。」 「也好,你與母親向來生分,作為媳婦是該去主動討長輩歡喜。」 話音剛落,阿銀便拉著他要去玩剛剛從外面買回來的花燈。 蕭徹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,無奈走了。 彈幕狂歡: 「太好了!我就知道女主還是舍不得男主的,她愛了這麼多年,怎麼可能輕易和離。」 「男主太隱忍了,這個奸細擅毒,他害怕她會對女主不利,為了女主的安全只好裝作自己對她毫不在意,不敢透露出自己的愛。」 「男主剛剛的眼神好讓人心疼嗚嗚嗚,他明明超愛的,那盞花燈原本是偷偷買給女主的,那女人死纏爛打才要去的。」 「女主再熬一熬就好了,等男主策反這個奸細,拿到羌戎的軍防圖你們就能 HE 了!」 可下一秒,彈幕齊齊停滯了一瞬。 因為我把那封和離書放在了蕭老夫人面前。 老夫人原本因為我的打擾不悅。 此刻嘴角卻控制不住地上揚,還在假模假式地問:「你這是什麼意思?」 我淡淡道: 「老夫人,我知道你一向不喜我,如今我也想通了,不合適的兩個人硬湊在一起,慢慢地,愛也成了怨。我想請老夫人幫忙,讓蕭徹簽下這份和離書。」 如果真如彈幕所說。 蕭徹所做的一切都是逢場作戲,他心里一直愛我,那他一定不會輕易答應和離。 可讓老夫人幫忙就不一樣了。 從我進蕭家門的那天起,她就日夜盼著我離開,我相信她不管用什麼辦法都會讓我成功和離。 剛剛還對我不耐煩的老夫人收起和離書,看我的眼神都和氣了許多。 「你能想通最好,我會想辦法讓徹兒簽下的。」 得到她這句話,我便起身告辭。 出門前想起什麼,回頭看了一眼: 「老夫人的安神香若是用完了,派人去我陳家醫館取吧,我明日將方子寫下。」 她微微一愣。 在我離開前叫住我。 張了張嘴,卻只是嘆了口氣。 「蘊娘,你是個好孩子。」 「只是我蕭家名門望族,如今式微,所有希望都在徹兒一人身上,他需要一個對他有所助力的女人,而不是……」 而不是我這個郎中的女兒。 我沒再說話。 對她點點頭后抬腳走了出去。 這一刻,如釋重負。 2. 彈幕卻急了。 「女主真要走?那男主怎麼辦?他會瘋的!」 「女主是不是傻啊!只要男主拿到羌戎的軍防圖就能在下次大戰中大展拳腳,得到皇帝信任從此節節高升,雖然還有幾年磨難,但只要熬過去,就能跟男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啊。」 「男主現在雖然在陪那女人,但他心里一直在想你,你不要一時糊涂啊。」 「男主的隱忍太讓人心疼了,愛卻不能說。一開始他為了娶女主,在蕭家族老面前跪了三天三夜,女主每次被婆母刁難罰跪,男主半夜都會心疼地給她抹藥,他這麼好,女主怎麼忍心不要他啊。」 「女主太不懂事了,就不能忍這一次嗎!」 …… 忍這一次嗎? 可是,我已經不記得我到底忍了多少次了。 嫁進蕭家那天,蕭老夫人跟族老沒有一個人露面,管家以大門年久失修打不開為由,讓花轎走側門。 眾所周知,只有妾室的轎子會從側門進。 我愣在花轎里。 蕭徹骨節分明的手挑起轎簾,他抱起我,大步向前,一腳踹開了蕭家的大門。 然后轉頭宣告眾人: 「陳蘊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,我這一生,有且只有她這一個妻子。」 那時我靠在他劇烈跳動的胸膛上。 對上他堅毅篤定的眼。 真的以為可以依靠他一輩子。 我愛芍藥,他親自選苗,種了一院子芍藥。 蕭老夫人不喜歡我,我去問早安,便讓我在日頭底下等著。 蕭徹眾目睽睽下拉走我,恭順道:「既然母親還沒起,那我帶蘊娘晚上再來。」 這麼一來,老夫人干脆讓我不要再去了。 我閑不住,他便陪我去醫館坐診。 我看病,他撐著腦袋看我。 那時誰看了都打趣,陳家醫館白撿了護院,有定國候世子坐鎮,誰敢來搗亂。 我的確過了一段時間無憂無慮的日子。 直到定國候病逝,蕭徹進了官場。 他開始變多的應酬,開始笑得虛情假意,開始忙到沒時間回家。 我去接他,碰見丞相夫人,無意間跟她戴了同一樣式的玉簪。 蕭徹抬手便將玉簪拂落在地,碎成幾段。 他皺眉: 「你與她出身云泥之別,戴一樣的玉簪自然會惹人不喜。」 我愣住了。 這簪子是他送給我的第一件禮物。 當時他耳尖通紅替我簪上的樣子我還歷歷在目。 他卻忘了。 他不在家,族老跟蕭老夫人便找起我的麻煩。 日日挑刺,不是讓我跪祠堂,就是讓我在太陽底下站規矩。 他應酬醉酒回來,酒勁上來,將我撲倒在床上,意亂情迷間盯著我的臉微微有些不悅:「你是我妻,以后少不了見客,怎麼也不好好收拾一下自己,膚色好像暗沉了許多,回頭我問問雀兒你們女人都用什麼面脂……」 他沒說話就睡了過去。 可我卻躺在一旁。 一顆心沉到谷底。 雀兒,春風樓的頭牌姑娘。 他們官場上的應酬免不了要去這些地方,推杯換盞,左右逢源,別人懷里抱著姑娘,誰能獨坐? 我只是心懷僥幸,想著蕭徹一定與旁人不同,他只是逢場作戲而已。 我不想深究,也不敢深究。 夜里醒來,我見他神色復雜地坐在我床邊。 正輕輕給我膝蓋上的淤青抹藥。 應當是從丫鬟那里聽說了婆母對我的刁難。 「疼嗎?」 我心里一暖,搖頭。 他欲言又止,沉聲道: 「以后多順著點母親吧,你也該懂點事了,以后也別去醫館坐診了,女人家本就不必拋頭露面。」 我愣住了,剛剛還不疼的,不知道怎的,突然疼得那麼厲害。 羌戎頻頻來犯,蕭徹為了更快地在朝堂站穩腳跟,自請上了戰場。 我日日在家里擔驚受怕。 三個月后,他平安歸來,卻帶回一個女人。 她叫阿銀,嫵媚活潑,美貌動人。 蕭徹說她是戰場上撿到的可憐人,帶回來做個丫鬟。 可阿銀從不做丫鬟做的事,她會在蕭徹洗澡的時候貿然闖進去,然后嬉笑著跑出來。 我特意做的糕點,蕭徹吃了半塊,阿銀便把那半塊咬過去,嫌棄地說太甜了。 蕭徹笑著看她吐舌頭,把糕點還給我: 「下次別做這麼甜了。」 他們日日待在一起。 我仿佛成了外人。 就在今日,我見蕭徹近日疲憊,給他熬了魚湯。 卻被阿銀搶過去喝了,因為太急被刺卡住,她捂著嗓子臉漲得通紅。 蕭徹立馬慌了神,他幾乎是下意識打翻了湯碗,剩下的魚湯全都灑在我手背上。 而他正掐著阿銀的臉,哄她張嘴,親手用筷子幫她夾魚刺。 我有些不知所措地呆站在旁邊,下意識移開目光。 卻無意對上老夫人的視線。 她看向我通紅的手背,沒有幸災樂禍,只是搖搖頭,仿佛在嘲笑我年紀輕輕,還不懂男人的本性。 晚上我因為燙傷疼得難以入睡,在院子里看月亮。 剛好碰到蕭徹帶阿銀出去。 「蕭哥哥,今天蘊姐姐好像被燙到了,都怪我,我們羌戎邊境窮,沒喝過這麼鮮美的魚湯,我一著急就被卡住了。」 「傻姑娘,別放在心上,你不知道,阿蘊有一手好醫術,她那手很快就會好的。」 「那就好,那我們快點走,慢了就趕不上花燈游船了。」 …… 我看著自己被薄紗包裹的手。 蕭徹說的沒錯。 我陳家世代行醫,我三歲起便跟著祖父學醫,習得一手好醫術。 這點小小燙傷對我來說只不過是一帖藥膏的事。 連疤都不會留。 可是蕭徹,我也會疼。 好疼啊,真的好疼。 祖父醫術高超,可他從沒教過我心上的傷又該怎麼治? 那些奇怪的文字說蕭徹愛我,他隱忍克制,為了以后的榮華富貴、功名利祿把對我的愛都深深藏在了心里。 他們說他都是在逢場作戲,以假亂真。 一個人做戲做久了,誰還能分清什麼是真什麼是假。 我愛蕭徹,更愛自己。 我從沒要過什麼榮華富貴、功名利祿。 我只愛他對我明目張膽的愛。 既然他要藏起來。 那我也不要了。 #大女主
我給啞巴總裁做話療,豪門全懵了
“封總家世長相哪樣不是頂級,只可惜,是個啞巴。” “真是苦了你了,姐妹。” “和封總結婚,你心里一定憋著氣吧?” 聽著對面人一番話說完。 桑鹿心頭突突直跳。 天吶! 居然和她昨晚夢境內容一模一樣。 夢中。
《失控》
當藝術生那年,我逼迫貧困生做我的身體模特。 我肆意擺弄著他,激情創作兩個月,然后,得知他竟是走丟的太子爺。 我怕了,連夜銷毀所有畫作放他自由。 後來,我跟他在畫展狹路相逢。 我低眉順眼:「承總好。」 男人冷笑:「怎麼,穿上衣服就不認識了?」 1 我沒想到會在我的畫展上見到承晝。 他穿著西裝,衣冠楚楚。 一個女人挽著承晝手臂,同樣衣著精致。 「這種完全就是打著藝術之名搞擦/邊。 「特別是這張,感覺就是事后畫的,真低俗!」 他們面前的這幅畫名叫「桎梏」。 畫布上。 一個蒙著黑色絲綢的男人跪在玫瑰花瓣上。 雙腿分開,頭顱高昂。 渾身未著衣縷,雙手被繩索牢牢捆綁。 承晝盯著這幅作品,面色陰沉。 我躲在不遠處的立柱后面,心臟跳到快要吐出來。 旁邊的女人還在添油加醋。 「聽說畫手還是個女的,真是夠不要臉的。你是不是也覺得很噁心?」 良久,承晝移開視線。 「嗯,是挺噁心的。」 獲得了共鳴,女人表情得意。 「我就知道你肯定看不上,怪不得這種畫室要倒閉。 「與其你投資這里,還不如投資我表哥。 「他是英國皇家美術學院畢業的,科班出身,怎麼都比這種野路子強……」 后面的話我沒聽到,女人挎著他的手臂走遠了。 直到確認兩人離開,我才從柱子后面走出來。 突然有人拍我肩膀。 「怎麼站在這兒了?」 是我工作室的經理人,祁延禮。 「我記得當初團隊對接,我明確跟你說過這幅畫不出展的,為什麼現在會在這里?」 聞言,祁延禮順著我的視線看過去。 心虛一閃而過:「是麼,我也不清楚,可能是工作人員……」 「祁延禮。」 見糊弄不過去,才道:「其實我一直不知道不展這幅畫的原因,腦袋被布遮住了,重點部位也全都被花擋上了,你怕什麼?」 我沒吭聲,他繼續說。 「你知道這幅畫現在多火麼,來這一半以上的人都是為了看他。 「夏清,我知道你有你的藝術堅持,但我是個商人,當時我們合作我也是看中了你的才華和野心。 「但近幾年你除了畫畫山水,就是畫畫花鳥。我承認你畫功精湛,但這種東西現在沒人看,我們畫室都要倒閉了。」 我沒被說動:「但我也記得我們當初合作的條件,是你不干涉我的任何創作。」 對視半晌,見我毫不退讓,祁延禮舉起雙手。 「Fine,我承認這次是我的問題,下不為例 Ok?」 事情已經發生,現在撤下來也沒有意義,我頭疼地按了按太陽穴。 祁延禮嬉皮笑臉搭上我肩膀:「安啦安啦,這次我們畫展效果不錯,我有預感這波肯定能拉到新的投資。」 幾天后,我果然接到祁延禮的電話。 說有人愿意投資我們的畫室。 「但對方有個條件。」 「什麼條件?」 「他要買『桎梏』。」 聽筒兩端陡然沉默下來。 祁延禮自覺理虧:「我和對方解釋這個不對外銷售,但人家堅持……」 「報價多少?」 「四萬八。」 祁延禮底氣不足,「價格是不高,但投資額是三千萬。其實我也納悶,這人也不缺錢啊,怎麼才開了這麼個價,是想要還是不想要……」 「可以。」 「什麼?」 「我說四萬八,我答應,賣了吧。」 畢竟這個價格。 就是當年我支付給承晝的價格。 #破鏡重圓
言言星耀
我爸是破產反派,最窮那年,他準備下海。 他把我留在出租屋,叮囑我。 「言言,爸爸去傍條大腿回來養你。你等著。」 可我一等就是三天。快餓死時,眼前忽然飄過一片字幕。 【反派出車禍昏迷不醒中,這小崽子怕是要餓死了。這可是他和惡毒女配的女兒。】 【也不怪惡毒女配,生孩子時,她爸媽把這孩子丟了,說她只生下了個死胎。她都不知道這孩子的存在。】 【她還領養了個孩子,把全部母愛都給了他。小崽子出去找爸爸,馬上就要被人販子拐走了,正好與惡毒女配擦肩而過。】 後來,人販子騙我走時,我直接沖過去抱住她的腿。 「媽媽!救命!」 1 我翻出袋子里最后幾塊餅干。 大喜趴在我腳邊,眼巴巴地看著我手里的食物,口水滴答。 「大喜,我們一人一半。」 我把餅干掰開,分了一半給它。 它舔了舔我的手,沒有立刻吃掉,而是用鼻子把餅干往我這邊推了推。 大喜是爸爸和我在菜市場救下的一只邊牧。 漂亮又聰明。 爸爸出門前,特意交代它看好我。 他說,幸運的話,會給我們傍條大粗腿回來養我們。 大粗腿是誰的大粗腿,我不知道。 只知道,爸爸好像很慘。 找工作一直找不到,就連掃大街都沒人要。 他說,有人在故意整他。 但是不要緊,為了我,他也會賺到錢。 爸爸說只出去兩個小時,可現在已經三天沒回來了。 我知道大喜也餓了。 上個月買的那袋狗糧早就見底了。 大喜這兩天都只吃我分給它的餅干渣。 「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啊?」 我揉了揉發酸的眼睛,小口小口吃完餅干。 窗外的天又黑了。 幸好有大喜,我不怕。 我兩把臉貼在玻璃窗上往下看。 等著爸爸從拐角出現。 但街角空蕩蕩的,只有幾個行人匆匆走過。 肚子又咕咕叫起來,我摸了摸癟癟的小肚子。 唉,好餓。 大喜的肚子也在叫。 爸爸是不是迷路了? 我對大喜說:「我們出去找爸爸吧。」 它嗚嗚的咬住我的褲腳,不讓走。 「可是我好餓,大喜,你陪我一起去好不好?我保證不亂走。」 它歪著腦袋,猶豫了下。 「汪!」 我給大喜系上牽引繩,把鑰匙掛在它脖子上,打開了門。 樓道里黑漆漆的。 大喜走在我前面,警惕地豎起耳朵。 到了樓下時,夜風一下子灌進我的領口,我縮了縮脖子。 該去哪里找爸爸呢? 大喜左右聞了聞,帶著我往右邊走去。 沒走幾步,我的眼前忽然一花,出現了一片字幕。 還帶文字轉語音。 奇奇怪怪的。 【反派出車禍昏迷不醒中,這小崽子怕是要餓死了。這可是他和惡毒女配的女兒。】 【也不怪惡毒女配,生孩子時,她爸媽把這孩子丟了,說她只生下了個死胎。她都不知道這孩子的存在。】 【她還領養了個孩子,把全部母愛都給了他。小崽子出去找爸爸,馬上就要被人販子拐走了,正好與惡毒女配擦肩而過。】 我心跳的有些快。 他們在說什麼? 反派是指爸爸嗎? 惡毒女配是誰? 我又是誰的女兒? 「大喜,你看見那些蚯蚓了嗎?」 我低頭問大喜。 它困惑地看著我。 他們說,爸爸出車禍了,在醫院里昏迷不醒。 我出去找他,會遇到壞人把我抓走。 而且,媽媽當時就在我旁邊。 爸爸不是說我和孫悟空一樣,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嗎? 他還說媽媽是菩提老祖,正在修煉中。 遲早有一天會找到我的。 不遠處,一個瘦高的男人鬼鬼祟祟地走了過來。 眼睛東張西望。 「小朋友,你怎麼一個人在這兒啊?」 他咧著一口大黃牙問我。 大喜立刻豎起耳朵,喉嚨里發出低沉的嗚嗚聲。 我心跳加速,抓緊了狗繩。 這個人會不會就是字幕里說的壞人? 「我在找爸爸,你是壞人嗎?」 我大聲問。 2 壞人出現了,媽媽是不是也會出現? 「呃……我怎麼可能會是壞人!」 男人表情一僵。 「哎呀,這麼冷的天,你爸爸可真不負責任。」 他搖搖頭,要來牽我手。 「叔叔帶你去找爸爸好不好?」 我退后一步。 爸爸說過,不能跟陌生人走。 但那些字幕說,遇到壞人時,媽媽就在旁邊。 「不行,我媽媽就在這,我要和媽媽一起去找爸爸。」 男人愣了一下,左右又看了一圈。 「就是你媽媽讓我來接你一起去找爸爸的。她就在前面的車里等著呢。」 我順著他的手指看去。 一輛黑色的車停在路邊。 彈幕: 【黑色車里坐著的正是這小孩的媽媽,好慘,明明剛剛還對視了一眼,卻錯過了。】 【天啊!真是命運般的相遇!】 【反派和惡毒女配的懲罰夠多了吧?都走到大結局了,還得虐他們!】 【就是,反派都被男主整的家破人亡了,連工作都找不到,惡毒女配生了孩子,卻不知道自己有孩子。】 我的心砰砰直跳,撒腿就往黑色轎車方向跑去。 大喜反應比我更快,拽著繩子幾乎把我拉得飛起來。 「哎!小孩!是前面那輛白色的車!」 男人在身后氣急敗壞地喊。 黑色轎車的車門正好打開。 一個長得很漂亮的阿姨牽著一個小男孩走了下來。 我毫不猶豫地撲上去抱住了她的腿。 「媽媽!救命!」 女人驚得差點摔倒,她身邊的小男孩也瞪大了眼睛。 「這是誰家的孩子?」 追過來的男人已經換上一副焦急的表情。 「哎呀,不好意思,這是我女兒,調皮跑出來了。」 他伸手要來拉我:「快跟爸爸回家!」 「他不是我爸爸!他是壞人!」 我死死抱住女人的腿不放:「他想把我抓走!」 男人發怒。 「別給人家添麻煩,快跟我走!」 「不然回家打死你!」 大喜立刻狂吠著撲上去咬住了他的小腿。 「該死的畜生!」 男人踢了大喜一腳。 「住手!我已經報警了,是不是你女兒,等警察來了再說。」 女人舉起手機。 「多管閑事!這是我家的孩子!」 男人慌了神,竟想強行把我拽走。 我嚇得尖叫起來。 就在這時,一直沉默的小男孩突然沖上去,一口咬住了他的胳膊! 「啊!小兔崽子!」 「快放開!老子打死你!」 男人痛得松開了我。 我驚呆了。 彈幕也傻了。 【臥槽!沈星耀不是輕微自閉癥嗎?】 【笑死!狗子咬左腳,他咬左手。】 【這咬人架勢也太兇殘了。】 周圍已經聚集了不少圍觀群眾。 白色面包車見勢不對,已經一腳油門溜走了。 等警察趕到時,那個男人已經被路人按在地上打掉了兩顆牙。 我看得很清楚,有一顆是被那個叫沈星耀的小男孩一腳踩掉的。 他好兇啊! 我們被全部帶回了警局。 媽媽就坐在我旁邊,她在安撫沈星耀。 我有點羨慕,眼巴巴的看著。 #女配

今日點擊榜
查看更多

植物人老公,我來了哈哈哈哈
相親群征婚,一個阿姨給她兒子找老婆,她家里 53 套房子收租,3 棟別墅,5 輛車,每個月給兒媳婦 10 萬零花錢,唯一的缺點就是她兒子是植物人。 我當場愛了,這哪是植物人啊,分明是我沉睡的王子! 王子,我來了! 1. 前段日子我進了一個相親群,進去湊數的,有什麼活動就去混吃混喝,增添人氣,平時也會看看信息,了解一下當代大齡青年們的愛恨離合。 群里也有一些老阿姨,幫自家兒女找對象的,其中一個老阿姨語出驚人,直接炸群。 她說家里 53 套房子收租,3 棟別墅,5 輛車,其余資產另算,全都是留給獨子的,并且以后會每個月給兒媳婦 10 萬零花錢。 全群轟動,各路姐妹齊齊冒泡,確認是不是真的。 阿姨說是真的,但他兒子是植物人,希望兒媳婦不要嫌棄。 群里瞬間啞火了,我卻樂了,這不是天降喜事嗎? 我本人早就決定不婚了,反正一個人無牽無掛,干啥不怕,結啥婚呢? 就算多一個植物人老公也無傷大雅。 我薛思思就是愛錢! 我立刻發信息:「阿姨,你瞎說什麼呢?你兒子哪里是植物人,他分明是我沉睡的王子!」 全群臥槽、鼓掌,又炸群了。 阿姨很快跟我私聊:「小姑娘真幽默,你真愿意嫁給我兒子嗎?不要逗阿姨哦。」 「嫁!」 「為什麼?」 「為了錢。」我也不整虛偽的,我就是為了錢。 阿姨沉默了,我還以為她失望了,不想她沒一會兒就給我轉賬 888 元,說是給我當車費,讓我去碧桂苑星月灣 8 號別墅見她,她會好好招待我的。 碧桂苑星月灣是我們這城市最好的別墅區,均價得 6 萬以上,阿姨果然是個有錢人啊。 我不客氣地收了錢,出發! 2. 到了星月灣,我找到了 8 號別墅,那富麗堂皇的貴氣撲鼻而來,搞得我都有點緊張了。 簡單地整理了一下頭髮和衣領,我摁響了門鈴。 一個四十多歲的靚姨來開門,笑容滿面的。 有錢人就是不一樣,四十多歲保養得跟三十出頭一樣,感覺皮膚比我還要好,打扮什麼的也是一頂一的時髦。 我跟靚姨握手,自我介紹一下:我叫薛思思,本地人,985 大學畢業生,正在努力考公。 靚姨打量我,第一印象挺滿意:「年輕又漂亮,還是名牌大學生,又是本地人,很好啊。」 我謙虛一番,跟她進屋子去。 她給我倒了茶,問了很多問題,無非就是家庭、工作之類的。 我父母早就離異了,誰也沒要我,所以我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,至于工作,搞服裝設計,年薪二十來萬。 靚姨聽后連連點頭,也不問什麼了,只是帶我上樓去。 「這是要去看我沉睡的王子?」我問了一句。 靚姨回頭一笑:「是啊,他也是我沉睡的小王子。」 我們上到了三樓,進了一間臥室。 其實我對她兒子不感興趣,畢竟我薛思思只認錢,她兒子我會盡義務照料好的,別的就純路人了。 結果看見她兒子的第一眼我就愣住了,荷爾蒙都開始涌動了。 我滴龜龜,這也太帥了吧? 緊閉的雙眼透出的長睫毛、柔和的臉頰上點綴著的精致五官、細長脖頸上清晰可見的鎖骨…… 這……王子,我滴王子! #甜文
滿分丈夫我不要了
婚后五年,顧時清一直是眾人口中的滿分丈夫。 除了是個工作狂。 直到那一天,公司團建一起玩真心話大冒險,新來的實習生非要拉著我一起裝醉,給各自對象打求助電話。 顧時清的電話甚至沒打通,在響了幾聲后被掛斷,只給我留下了一句「忙。」 而下一刻—— 「我這就來接你。」 熟悉的嗓音從綠茶實習生的手機里傳來。 我抬眸望去,是對方挑釁的目光。 我想,這段婚姻該結束了。 1 公司團建我是臨時決定參加的。 玩了一天,很累,本想吃完飯就可以回家休息,一個女生卻突然擠到我身邊。 我剛要往旁邊挪一挪,就有人提醒那女生,「宋曉維,這位是咱們沈副總裁,你別擠到沈總了。」 我露出微笑,「沒關系,出來玩沒大小,大家自在一點……」 叫宋曉維的女生已經在我身邊坐下了。 她長得很漂亮,一笑的時候一雙大眼睛水汪汪的,澄澈干凈,著實討人喜歡。 我笑著問她,「你是新來的?」 宋曉維朝我伸出手,「我是新來的實習生,今年才二十一歲。」 我點點頭。 宋曉維突然說:「咱們玩真心話大冒險吧,沈副總,咱倆給大家打個樣。」 都不等我開口,她就徑自拿起我放在一邊的手機遞給我,微微挑眉,「大冒險,敢嗎沈副總?」 我有點欣賞她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,再加上大家都在,就沒掃興,接過手機。 「怎麼玩?」 「我們兩個裝醉,給對象打電話來接。」宋曉維躍躍欲試,說話的時候總帶著一股錚錚昂揚的勁兒。 我接觸的人多了,精準又敏感地從她這股勁兒里挑出了一絲得意和挑釁。 傳聞中那些要整頓職場的年輕人也來我公司了? 我沒生氣,只是覺得有點好笑,然后就找出顧時清的號碼撥過去。 因為是玩大冒險,我開了免提。 周圍有人開始調侃。 「宋曉維,你跟咱們沈總玩這個游戲可是自取其辱了。」 「你還沒見過咱們顧總吧?是沈總的老公,絕對的二十四孝好老公。」 「別說裝醉了,就算什麼事沒有,沈總一通電話,顧總也立馬就會放下手里的事情過來。」 …… 他們說話的時候,我手機里的忙音一直在響。 電話沒打通,那邊掛斷了。 緊接著我收到了顧時清發來的一條微信,只有一個字:【忙】。 我笑了出來:「我輸了。」 「該我了。」宋曉維聲音微微上揚。 好幾個人都在給她使眼色,讓她別打,可宋曉維到底年輕,不知道職場的潛規則,也不懂人情世故。 電話接通了。 宋曉維的聲音再次響起,變得甜膩而綿軟:「我喝醉了,你來接我好不好?」 她說完才側頭,迎上我的視線,下巴微揚,眉梢輕挑,標標準準的挑釁表情。 我意識到,這個宋曉維似乎有點針對我。 可我不知道她的針對從何而來。 因為,我之前沒見過她,她以后除了集體活動,應該也沒機會見到我。 下一秒,宋曉維的手機里傳來一道男聲。 「我這就來接你。」 低沉的嗓音讓我身子一僵,像是好端端地走在大街上,被人平白無故澆了一盆冰水。 這道聲音我再熟悉不過了,是我的老公。 顧時清。 「好啊,我等你。」宋曉維掛斷電話,再次看向我,眼角眉梢的得意和挑釁完全浮現出來,沒有一絲遮掩。 像是打了勝仗的將軍。 我一下子便明白了她的針對從何而來。 哦,原來她不是來整頓職場的,而是想來整頓我的婚姻。 #大女主
穿成惡女后每天都在洗白
穿越成花癡,醒來就是爬床現場,唐竹筠轉身就跑——這床不爬了! 開玩笑,她爹是狀元,哥哥是狀元,兒子還是狀元,罩著她橫著走,要什麼男人? 身為神醫,專心搞事業,救死扶傷,男人退散! 晉王哀怨臉:說好的要爬床,本王等了個寂寞。 「秀兒,是你嗎?」 唐竹筠睜開眼睛,只覺得眼冒金星,雙膝火辣辣的疼,看著面前神色焦急的丫鬟,試探著喊了一聲。 她,二十二世紀的名醫,剛通宵做完兩臺手術,去食堂吃飯的時候滾下臺階,原本以為是大型社死現場,沒想到卻是穿越現場。 頭腦中立刻涌入了許多并不屬于她的記憶。 她叫唐竹筠,二十歲,大理寺卿唐明藩之女,京城中赫赫有名的恨嫁女花癡。 可憐唐明藩一代賢臣,兩袖清風,卻被這個不成器的女兒弄得早生華發,名聲掃地。 「姑娘,您沒事吧,嚇死奴婢了。」秀兒驚魂未定地道,伸手要扶她起來。 完了,是真的穿越了。 來不及感慨,唐竹筠只想拔腿就跑。 因為她是被門檻絆倒摔了一跤,而現在屋里床上正躺著一個不省人事的男人,也是她的目標——晉王。 前身作死恨嫁,把京城四公子騷擾了個遍;不久前皇上流落民間的兒子晉王認祖歸宗,豐神俊朗的模樣就被愚蠢的前身惦記上了。 今日是大長公主府的賞花宴,目標主要是給這位晉王擇妃,唐竹筠吃了熊心豹子膽,把這位爺放倒了,現在進入了爬床階段。 「走,快走!」唐竹筠爬起來,抓起地上丟的荷包,看到有白色粉末,還舉起來聞了一下,然后沒多看一眼床上英俊的男人,揣好荷包,拉著秀兒就往外跑。 「不是,姑娘,您不是……晉王就在那里啊!」秀兒呆呆地看著唐竹筠。 「讓你走你就走!」唐竹筠道。 來不及解釋了,快跑! 「姑娘,您不反悔了?」秀兒不確定地道,「您不是要睡晉王嗎?」 「我嫌命長啊!我想睡不能去睡小倌兒嗎?」 「可是您之前去,因為沒錢被趕出來了……」秀兒小聲地道,「小倌兒要錢。」 「睡小倌兒要錢,睡晉王要命!你再啰嗦我就自己走了。」 #一樓免費看全文
野火燎原.
高考完全班去旅游,愛慕竹馬的轉校生卻在洗澡時意外發生火災,被困在浴室向竹馬求救。 竹馬男友不顧危險執意沖進去救她。 我攔住他,好心相勸:「火勢太大,你會有危險的!我已經叫了消防員來滅火。」 竹馬冷靜了下來,沒再沖動。 後來轉校生光著身子被消防員救下,不但不感謝,還哭訴清白都被他毀了。 她喊來竹馬告別:「江嶼白,來世我再清白地愛你,你要記得等我。」 她自覺受辱,選擇跳🏢自盡。 十年后,我生產危急之際,竹馬卻不肯簽字手術。 他說:「這是你欠瑤瑤的,都怪你當初阻止我,為什麼死的人不是你!」 害我一尸兩命。 他竟為了轉校生恨了我十年。 所以重活一世,我學乖了。 不再阻止他,他沖進火場救人的時候。 我還貼心地替他們把門關上了。 1. 生產那天。 醫生說我胎位不正,情況危急。 「必須要家屬簽字才能給你做剖腹產。」醫生一臉抱歉。 隔著門,我卻聽見竹馬江嶼白說:「不簽!這是她應該承受的,醫生你不必再勸。」 那語氣,仿佛我是他的仇人。 我不明白他為何如此狠心。 身體的疼痛快要讓我喘不過氣。 我用盡全身的力氣大喊:「小白,你快簽字啊!真的好痛,我沒力氣了,不簽字我會死的!」 「痛就對了,這都是你欠瑤瑤的,都怪你,當初火災不讓我進浴室救她,導致她被消防員看光,害得她抑郁跳🏢!」 「為什麼當年死的人不是你!」他突然生氣大喊。 瑤瑤。 我已經多少年沒聽過這個名字了,差點都想不起來這是誰。 原來,他從未忘記過她。 還將她的死,全算到我頭上。 他竟如此恨我,恨到希望我死在手術臺上。 眼淚無聲地從眼角滑落。 身心交瘁,我突然間失去了所有力氣和手段。 仔細想想,其實一切早有預兆,是我太傻。 2. 「晚星,你就是太善良了,你看沈瑤那賤樣,要換我早一巴掌扇過去了!」 「她明知你和江嶼白在一起了,還總纏著他,看,現在她又去勾搭他了。」 再一次睜開眼,看到的就是年輕版的閨蜜林夏。 她正朝我擠眉弄眼,示意我往右看。 我下意識轉頭。 兩人靠得很近,沈瑤胸前鼓鼓囊囊的。 隨著她的動作,時不時地蹭到江嶼白的手臂。 我咬緊了嘴唇,拳頭不自覺地緊握。 恍惚了好一會兒。 看到活著的沈瑤和旁邊無盡的大海。 我才意識到,我竟然重生了。 回到了高考完班級去海邊出游的時候。 那場讓江嶼白耿耿于懷的火災,正是發生在這里。 眼角有些濕潤。 江嶼白,這一次,我一定要離你遠遠的! 此刻,江嶼白也剛好抬頭,似有所感。 朝我這邊看過來,見到是我。 便立馬拉開了和沈瑤的距離。 他解釋道:「星星,你別誤會,她在和我對高考的答案,想要估分。」 我淡淡地笑了,說:「江嶼白,我沒誤會啊,你慌什麼?」 聽到江嶼白迫不及待的澄清,以及看到被拉開的距離,沈瑤看起來有些失望和不甘心。 她一臉不滿地說:「蘇晚星,他不過是和我多說了幾句話而已,你有必要嗎?」 「怎麼沒必要?嘖嘖,貼那麼近,某些人恨不得把自己免費送出去吧,只可惜別人不要。」林夏忍不住翻了個白眼。 「你!你可真齷齪!」她尷尬地臉紅了。 周圍人聽到這邊的吵鬧,紛紛圍過來。 然后開始七嘴八舌的議論起來。 「嘖嘖,沈瑤可真浪,胸這麼大還穿個低胸裝,就是為了勾引江嶼白吧。」 「江嶼白這小子可真有福氣,羨慕死我了,讓班里兩個大美女為他爭風吃醋。」 「沒見過像沈瑤這麼賤的,江嶼白都拒絕那麼多次了,她還不死心呢,就喜歡勾搭別人男朋友的這種背德刺激感是吧。」 我看見江嶼白憤怒地揮了揮拳頭,大聲阻止道:「夠了,都給我閉嘴!我只喜歡蘇晚星一個人!」 然后便冷冷地對沈瑤說:「你以后離我遠點,我不想讓星星誤會。」 沈瑤一副泫然欲泣的模樣,倔強地咬著嘴唇。 江嶼白的臉上頓時露出了一絲心疼,雖然不過幾秒,但還是被我捕捉到了。 和上一世一模一樣的場景上演了,就連對話,也毫無區別。 不過這次,我作出了不一樣的反應。 #重生 #渣男 #大女主
我真的沒婚變啊
得知方瑾文青梅回國的那一刻,閨蜜給我發了幾十秒的語音方陣。 「程嘉嘉,快收拾收拾,你老公白月光回來了,你馬上就要被逐出家門,趕緊請律師跟他對打。」 可我那時正窩在方瑾文懷里看電影。 這下電影也不看了,直接掰開身后人環在我腰上的手:「他們說你要跟我離婚,還要找律師打我。」 方瑾文懶洋洋的神情忽然間充滿疑惑,徑直把我手機拿過去。 手機仍然在震動,是閨蜜發過來的各大群聊截圖。 「兩年時間已經足夠程嘉嘉撈不少了吧,做人還是要識趣點。」 「唉,沖動結婚不可取啊。」 「方少又不是沒有賭氣的資本,離了也就是分點錢的事。」 ...... 截圖看完后,方瑾文脫口而出:「我靠,神經病啊。」 01 罵了,氣沒消。 他索性穿好衣服,拿上車鑰匙就往外走,說要親自會會截圖上鬧得最歡的幾個人。 我沒意見。 這種事,當然是他出頭最好。 我嘛,安心看電影就行。 還缺了點什麼。 我喊來保姆萍姐,讓她幫我洗點草莓。 草莓端過來時,一向穩當的萍姐竟然手抖了一下。 我連忙接住果盤,又抬頭看了看萍姐,以為她沒休息好。 不看不知道,一看才發現她的眼睛有些紅紅的。 「姐,怎麼了?」 她看著我,欲言又止,最后幽幽地嘆了口氣: 「太太,我雖然只跟了你兩年,但我心里一直是很認你的,如果你日后真的離開這家,能不能帶我過去,當是續聘?」 我一頭霧水:「我不走啊,我哪兒也不去啊。」 「對,對!就得這樣,」萍姐突然來精神了,「只要心夠硬,誰也搶不走你的地位。」 我愣了會,才明白過來,只是看個電影的功夫,我好像和外面的世界脫節了。 此時,閨蜜安月更是直接撥通了我的電話: 「嘉瑜,我剛剛不是建議你請律師嗎?你看我怎麼樣?好歹是自己人,信得過。」 「對了,你有簽婚前協議嗎?」 「簽了也沒關系,我努努力,還是能有轉機的,畢竟是你老公婚內有過錯在先……」 我默默地聽了會,對她說:「把視頻開開。」 「面談是嗎,好嘞。」 可視頻打開后,我的臉并沒有出現在屏幕里面,只能看見正在揀水果的右手。 安月迷惑極了:「手指頭都在啊,怎麼了?」 我展開手掌:「看上面的鴿子蛋啊!定制款!七位數!我老公昨天才送我的,哪里像是要離婚的樣子。」 安月點了點頭:「我明白了,被告他目前是有一個補償的行動是吧?」 「不是補償!他經常給我送東西的。」 「嘉嘉,我理解你現在的心情,但過去是過去,而現在的情形跟以前不一樣了,你不能一直逃避下去的……」 我深深地呼了口氣。 然后毅然地關掉視頻。 終于清靜了。 但我有預感,這事遠遠沒完呢。 #甜文

熱門好書 百聽不厭
換一換


最新上線 搶先入耳
查看更多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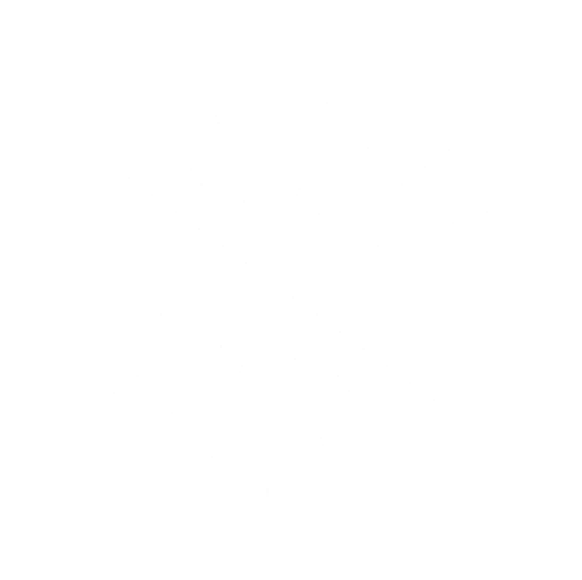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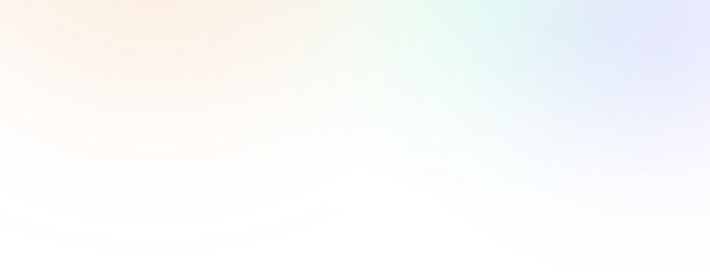
 暢享閲讀盛筵!
暢享閲讀盛筵!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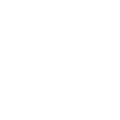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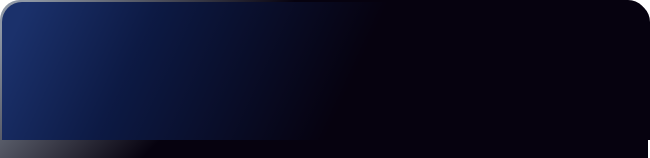





 聯繫客服
聯繫客服
